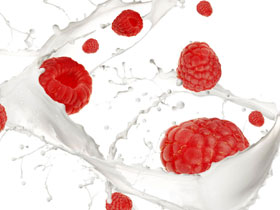摘要:蜂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流行性的少数几种自然疗法之一。蜂胶中的药理活性分子是类黄酮和酚酸及其酯。这些成分对细菌,真菌和病毒有多种作用。另外,蜂胶及其组分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活性。此外,蜂胶已被证明可以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然而,要证实这些说法的临床研究是必需的。
关键词:蜂胶,老年和现代医学
1.介绍
术语蜂胶来自希腊专业人士(在'前面','在'入口处'')和城邦('社区'或'城市'),并且意味着防御蜂房的物质。蜂胶或蜂胶,是由工蜂从白桦,杨树,松树,al木,柳树和棕榈等多种树种的叶芽中收集的棕色树脂材料。为了生产蜂胶,蜜蜂也可以使用植物积极分泌的物质,或者从植物伤口渗出(叶子上的亲脂物质,粘液,树胶,树脂,格子等)。一旦采集到,这种材料富含唾液和酶促分泌物[1],并被蜜蜂用来覆盖蜂巢壁,填补裂缝或缝隙,并防止杀死的入侵昆虫。
蜂胶是自古以来广泛使用的天然补救剂。埃及人非常了解蜂胶的抗腐败性能,并用它来保护尸体。蜂胶被希腊和罗马的医师Aristoteles,Dioscorides,Pliny和Galen公认为具有药用价值。这种药物在伤口治疗和口腔消毒剂中用作防腐剂和愈伤剂,这些用途在中世纪和阿拉伯医生中持续存在。蜂胶也得到了与旧世界文明无关的其他人的承认:印加人采用蜂胶作为抗发烧剂,而十七世纪的伦敦药典列举了蜂胶作为官方药物。在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该药因其抗菌活性而在欧洲非常流行。
现代中医认为其抗菌,抗真菌,抗病毒,保肝和抗炎特性,增加人体对感染的天然抵抗力,并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外用蜂胶可缓解由细菌和真菌引起的各种类型的皮炎。
今天,蜂胶目前被用作流行补救剂,并且以胶囊的形式(以纯形式或与芦荟凝胶和罗莎犬或花粉组合),作为提取物(水醇或乙醇酸),作为漱口水(与蜜蜂花,鼠尾草,锦葵和/或迷迭香),以润喉糖,面霜和粉末形式(一旦溶于水中用于漱口水或用于内服)。它也可作为纯化产品在蜡中除去。据称蜂胶还可用于化妆品和保健食品的成分。
2.化学成分
到目前为止,已有180多种化合物,主要是多酚,已被确定为蜂胶的组成成分。主要的多酚是类黄酮,伴随着酚酸和酯,酚醛,酮等。蜂胶中的其它化合物是挥发性油和芳香酸(5-10%),蜡(30-40%),树脂,香脂和花粉谷物是镁,镍,钙,铁和锌等重要元素的丰富来源[2]。从巴西(3,5-二苯基-4-羟基肉桂酸)和中国蜂蜡(二十八烷醇)样品中也分离出新的化合物。虽然近年来蜂胶的化学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已得到澄清,但仍存在一个问题,即其化学成分的显着变化取决于其收集的位置。
蜂胶的抗微生物特性似乎主要归因于类黄酮pinocembrin,高良姜素和松鳞菌素。Pinocembrin还具有抗真菌特性。其他活性化合物是香豆酸和咖啡酸的酯。在其他化合物中,异戊烯基对香豆酸和二萜酸具有抗细菌和细胞毒活性。咖啡酰奎尼酸衍生物显示出免疫调节和保肝作用,呋喃木酚素木脂素抑制一些细菌的生长。咖啡酸苯乙酯(CAPE)也对肿瘤细胞具有细胞毒性。
3.药理学性质和毒性
蜂胶制剂显示在体外抗微生物活性,主要对革兰氏阳性(葡萄球菌和Strepthococci属)和革兰氏阴性细菌(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夏枯草和铜绿假单胞菌),幽门螺旋杆菌,原生动物(Ť cruzi),真菌(白色念珠菌)和病毒(HIV,疱疹病毒或流感病毒)。Tosi等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3]表明用于提取蜂胶的溶剂可能影响其抗微生物活性的效力。事实上,该油剂具有广泛的抗微生物活性; 甘油溶液对革兰氏阳性菌的抑制作用很小,而乙醇和丙二醇溶液对酵母菌显示出良好的活性。研究还表明,蜂胶对链霉素和氯唑西林的抗菌活性具有显着的协同效应,并且在含有固定量的标准菌株的培养基中对氯霉素,头孢拉定和多粘菌B的抗菌活性具有中等协同效应金黄色葡萄球菌[4]。还对15种牙科临床相关性菌株进行了研究:蜂胶提取物显示出体外抗菌活性,抑制细胞粘附和抑制水不溶性葡聚糖形成[5]。与蜂胶提取物相比,山金车提取物在这三种条件下仅略有活性。
众所周知,生殖器HSV感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难以治疗的疾病。Vynograd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6]表明,含有蜂胶的软膏能有效治愈生殖器疱疹病变和减少局部症状。用蜂胶提取物或软膏进行局部治疗不仅可用于治疗疱疹感染,还可用于牙科,皮肤科和耳鼻喉科[6]。
蜂胶还对急性和慢性炎症模型(甲醛和佐剂诱导的关节炎,角叉菜胶和PGE 2诱导的爪水肿,棉托盘肉芽肿)表现出抗炎作用。蜂胶的抗炎作用的确切机制仍不清楚。最近,Rossi等人 [7]证明,蜂胶以浓度依赖性方式抑制来自盐水或LPS处理的大鼠的肺匀浆物的COX活性。在测试的化合物中,只有CAPE和高良姜素有助于蜂胶的抗炎活性; 然而,CAPE的贡献更大。
蜂胶在体外对巨噬细胞表现出免疫刺激和免疫调节作用[8,9],而体内则增加了小鼠CD4 / CD8T细胞的比例[10]。
这一范围的效应可以解释蜂胶用于口腔中慢性和急性炎症,牙周炎,鼻窦炎,pharingotracheitis或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疾病以及皮肤溃疡的基本原理[11-13]。蜂胶对四氯化碳诱导的大鼠急性肝损伤和对乙酰氨基酚和烯丙醇引起的小鼠急性肝损伤也有保护作用[15]。已知肝GSH对化学诱导的细胞损伤具有保护作用。GSH是肝脏中最重要的抗氧化分子之一,并且在生理浓度下有助于维持细胞的正常氧化还原状态。蜂胶能够逆转对乙酰氨基酚在小鼠中诱导的GSH消耗,从而防止细胞死亡。
蜂胶也可以作为抗氧自由基的清除剂[16]。最近的研究表明,蜂胶能够抑制β-巯基乙醇自氧化过程中产生的超氧化物阴离子的形成[17]。在这些研究中,CAPE在抑制超氧化物阴离子的形成方面比高良姜素更有活性。CAPE还可以防止家兔肾下主动脉阻塞后的缺血性脊髓损伤。该实验结果提示预防性使用蜂胶及其活性化合物CAPE以避免在胸主动脉瘤或胸腹主动脉瘤手术修复过程中出现这种并发症[18]。
蜂胶还具有类似于可卡因的麻醉作用[19],并显示出对生物组织的再生作用[20,21]和抗许多癌细胞的抗肿瘤活性[10,22-24]。蜂胶也能够抑制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25]。CAPE也被认为是具有化学预防和抗肿瘤特性的蜂胶中的主要活性化合物之一[24]。然而,蜂胶及其组分CAPE对癌症治疗的积极作用的确切机制还不完全清楚,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在低剂量下蜂胶被认为是安全的:然而,在超过15克/天的剂量下,副作用是常见的。最常见的副作用是过敏反应,以及皮肤或粘膜刺激。谨慎应该用于治疗哮喘患者以及湿疹和荨麻疹患者。
4.未来的观点
据报蜂胶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后者在停药后可持续几周[26]。这些意想不到的活动使蜂胶前瞻性地成为用于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非常有趣的化合物。动脉粥样硬化被认为是一种多因素疾病,其发病机制不能被公认的经典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饮食,吸烟等)彻底解释。今天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免疫发病机制。另一方面,一些数据表明单核细胞活化可能在动脉粥样硬化进展中发挥作用[27]。炎症,单核细胞活化和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一种微生物制剂,例如衣原体肺炎,幽门螺杆菌或巨细胞病毒(bacterioscleroris)。细菌可以释放激活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的脂多糖(LPS)。活化的内皮细胞在其表面上表达血管内皮细胞粘附分子(CAM),例如选择素和整联蛋白,其促进血液单核细胞的滚动,粘连和最终外渗。另一方面,LPS促进单核细胞活化并释放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前列腺素,其刺激平滑肌细胞迁移并增强内皮细胞表面上的CAM表达。鉴于蜂胶对细菌和炎症具有活性,并能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减少细胞凋亡[9],因此可将其作为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全球补救措施”。
5。结论
古希腊和罗马医生的着作中提到了蜂胶的有益作用。几个世纪以来,蜂胶也被用于多种不相关的人类疾病。例如治疗肺结核,十二指肠溃疡和胃紊乱,并减轻各种类型的皮炎并减少发烧。然而,两种用途持续了几个世纪:主要的用途是作为防腐剂和防腐剂的外用; 第二个是内部用于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除了这些用途,蜂胶似乎也为炎性疾病患者提供益处。临床研究现在也在进行中,以验证蜂胶在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参考
[1] V. Bankova,SL De Castro,MC Marcucci Apidologie,31(2000),第3-15页
[2] JW Dobrowolski,SB Vohora,S. Kalpana,SA Shah,SAH Naqvi,PC Dandiya J Ethnopharmacol,35(1991),pp.77-82 <
[3] B.Tosi,A.Domini,C.Romangnoli,A.Bruni Phytother Res,10(1996),第335-336页
[4] W. Krol,S. Scheller,J. Shani,G. Pietsz,Z. Czuba Arzneim-Forsch,43(1993),第607-609页
[5] H. Koo,BP Gomes,PL Rosalen,GM Ambrosano,YK Park,JA Cury Arch Oral Biol,45(2000),第141-148页
[6] N.Vynograd,I.Vynograd,Z.Sosnowski Phytomedicine,7(2000),第1-6页
[7] Rossi A,Longo R,Russo A,Borrelli F,Sautebin L,2002. Fitoterapia。在新闻。
[8] V. Dimov,N. Ivanovska,V. Bankova,S. Popov Vaccine,10(1992),第817-823页
[9] R. Claus,R. Kinscherf,C. Gehrke,et al。 Arnzeim-Forsch,50(2000),第373-379页
[10] T. Kimoto,S. Arai,M. Kohguchi,等人。 Cancer Detect Prev,22(1998),506-515页
[11] SVKosenko,TIKosovich Stomatologia(Mosk),69(1990),第27-29页
[12] Z. Szmeja,B. Kulczynski,Z. Sosnowski,K. Konopacki Otolaryngol Pol,43(1989),第180-184页
[13] J. Serkedjieva,N. Manolova,V. Bankova J Nat Prod,5(1992),第294-302页
[14] R.冈萨雷斯,科科,D.雷米雷斯等人。 Phytother Res,9(1995),第114-117页
[15] D.雷米雷斯,R.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等人。 Phytomedicine,4(1997),第309-314页
[16] C.Pascual,R.Gonzàlez,R.Torricella J Ethnopharmacol,41(1994),第9-13页
[17] A. Russo,AA Izzo,V. Cardile,F. Borrelli,A. Vanella Phytomedicine,8(2001),pp.125-132
[18] A. Ilhan,U. Koltuksuz,S. Ozen,E. Uz,H. Ciralyk,O. Akyol Eur J Cardio-Thorac Surg,16(1999),第458-463页
[19] M.Butz,J.Metzner Pharmazie,34(1979),第836-841页
[20] A. Stojko,S. Scheller,I. Szwarnowiecka,J. Tustanowski,H. Ostach,Z. Obuszko Arzneim-Forsch,28(1978),pp.35-37
[21] S. Scheller,A. Stojko,I. Szwarnowiecka,J. Tustanowski,Z. Obuszko Arzneim-Forsch,27(1977),第2138-2140页
[22] AH Banskota,Y. Tezuka,JK Prasain,K. Matsushige,I. Saiki,S. Kadota J Nat Prod,61(1998),第896-900页
[23] AH Banskota,Y. Tezuka,IK Adnyana 等人。 J Ethnopharmacol,72(2000),pp.239-246
[24] YJ Lee,PH Liao,WK Chen,CY Yang Cancer Lett,153(2000),第51-56页
[25] NB Takaisi-Kikuni,H. Schilcher Planta Med,60(1996),第222-227页
[26] Ricchiuto GM,1994年。Le nuove frontiere della propoli。GMR Editore,维罗纳。
[27] APBurke,A.Farb,GTMalcom,Y.Liang,J.Smialek,R.Virmani N Engl J Med,336(1997),第1276-1282页
- 新渔公众号
- 微信扫一扫
-

- 新渔商城
- 微信扫一扫
-